評佛洛伊德1939《摩西與一神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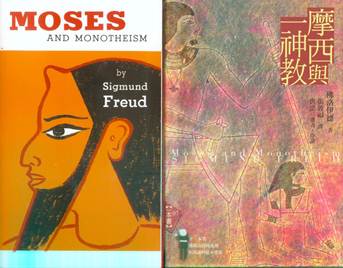
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專業中,神經症的發展公式:早期創傷à防禦作用à潛伏期à神經症發作à被壓抑事物的回饋。他同時也從宗教現象發現類似神經症—強迫症的現象,如現代耶路撒冷哭牆前不斷地自責,如不斷稱自己為罪人…,推測應該是宗教起源之前發生過重大的民族共同創傷。亦即曾經發生過重大的攻擊性事件,經過漫長的潛伏期之後,發生回饋作用。佛洛伊德在1939年出版《摩西與一神教》一書,稱期待彌賽亞降世的猶太教,其實本質上就是從摩西開始的摩西宗教。書中的許多推論,讓出版界、學界與猶太人群體都覺得不可思議,以致於無法接受。但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是如何想得呢?
 一,摩西是埃及人
一,摩西是埃及人
佛洛伊德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解釋,摩西故事的開始,是聖經故事的基礎。猶太人的回憶與補全成為摩西故事的前傳。依命名與英雄傳奇的塑造模式來說,佛洛伊德將摩西視為是埃及人。Mose,在埃及姓名中,是“…之子”,像是法老王Tuthmosis,意指Thoth神之子。Mose是否有猶太人原生家庭不得而知,但撫養家庭確定存在。就英雄故事編寫的理論而言,拋棄者與收容者,往往後者會創造英雄個性[1]。
二,摩西宗教是埃及式的宗教。
摩西是否可以一人之力創造新宗教? 或者他只是創造一種埃及式的宗教? 他提倡的宗教其實是埃及宗教多神信仰中的一支,只不過這支與其他的諸神宗教大大不同,它像是Akhenaten的新宗教,但是它隨著他的駕崩而消失。Akhenaten重現新的太陽神樣式,它不再是小金字塔與一隻鷹,而是光芒四射的太陽盤。其他的神祇信仰都被排除在外[2]。若說即得利益者,或是Akhenaten時期之被打壓者—分歧的地方性多神教的反撲力量,甚至是政府力量,如拉美西斯二世對Akhenaten太陽神教的無孔不入的摧毀行動,會是摩西出走的原因。
縱使如此摩西宗教中的割禮circumcision儀式,仍是埃及人習俗,這正是埃及宗教的融合特色。其他環以色列民族並無之,佛洛依德也認為這是他傳給猶太人。割禮是有健康好處的,它可以降低子宮頸癌的發生。
三,摩西被他自己所創立的宗教拋棄。
佛洛伊德引用Ernst Sellin在1922年的何西阿書論點,說塞林猜測摩西被猶太人謀殺[3]。何西阿書,先知轉述耶和華的憤怒,細數猶太人的罪行與偏離。Freud目睹以色列人受納粹壓迫,但也目睹以色列人如何以原罪說療癒整個民族的悲慘。這現象顯然是鼓舞了他的結果論認知,逆向証明應該有個源自遠古摩西時期原罪存在,就是弒殺了摩西。
 佛洛伊德先假設認為摩西如果是被殺的,那是因為防禦作用所致的。再根據塞林的猜測“摩西被猶太人謀殺”,縯繹出壓抑事件的回饋—預告了如摩西英雄般的救世主回來[4]。而摩西就是救世主的預表。
佛洛伊德先假設認為摩西如果是被殺的,那是因為防禦作用所致的。再根據塞林的猜測“摩西被猶太人謀殺”,縯繹出壓抑事件的回饋—預告了如摩西英雄般的救世主回來[4]。而摩西就是救世主的預表。
四,埃及宗教的啟發
埃及智慧理性之神,Thoth,的另一面就是月神。是感性的、瘋狂的象徵。這一體相對反兩面的性質,也是Moses宗教的性質。一個母系社會的民族,將圖騰從母親形象轉向父親形象,性質上是感性能力倒退,理性能力進步的過程。這會提高民族自信。父性與母性宗教的融合,是埃及宗教的特色,如amun與re神的結合。
佛洛伊德所謂的超我,就是對感性本能的控制。它產生超越、反對直接感知覺的作用,產生一種自豪與得意感[5]。一個原始民族需要一個部落的首領作為個人的保護者,這首領就是對超我的信仰。父親理性形象,是信仰的後盾。原本來自父母親的管制模式,發展成為社會式的、超我式管制的參考模型,它發展成權威體制—父權概念下的管制與克制模式。
Moses一神教的起源,是對偉人角色的期待。這偉人是父親形象的投射。但它卻是兒子式(mose)宗教。基督教相對於猶太教,就是兒子式的宗教。佛洛伊德為了成全殺基督,就是殺父上帝之子的事實導致壓抑情結,所以他必須主張摩西這位從神而生之子“mose”,也被弒殺。殺兒子的動機,根源於對父親的敵意,然後壓抑與傷痕形成猶太民族特有的原罪說。它源於身為唯一選民、離棄父親意念的罪惡、受寵願望的未能實現的三重加成的壓抑。殺耶穌的罪惡感,成為一種全民的共罪,這共同負罪感與拭殺耶穌的舉動,可以說是對父上帝的敵意壓抑所致。這是強迫性神經症反向作用的特點。耶穌真實存在,而“殺耶穌”作為媒介,可以讓猶太人對父上帝的幻覺與歷史真實的關係得以成全[6]。

結論
《摩西與一神教》書中,佛洛伊德再一次運用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如同他前本書《圖騰與禁忌》。書中,他主張摩西真的出生於古代埃及,並且是Akhenaten的後繼者,古代埃及的一神論者。但書中假設摩西被叛變的以色列人所殺,並且與其他的火山誕生性的一神宗教者結合。書中,Freud解釋,其實在弒殺摩西後的隔年,這些猶太人就後悔,所以開始期待彌賽亞的到來。這種殺摩西的原罪,讓他們對有期望救世主到來的願望。而這種行為,就是對“被壓抑事物的回饋”,如此回饋可以使他們感覺舒服些。

 思惟方法中的縯繹法,已經因為線性式因果關係的狹隘,而遭揚棄,因為它經不起各種可逆性的考驗。佛洛伊德則是直接訴諸逆向的推論,認為殺基督就是全民一起對於長久歷史之前的殺摩西事件的“壓抑事物的回饋”。殺基督的原因與意義,其實應該是有多元面相的。因此佛洛伊德的立論,是過於一廂情願、線性的認定。但是回到1930年代,佛洛伊德提出一神論觀點的時空環境來說,包含帝國主義式的侵略、演化論的線性發展,不也同樣是過於一廂情願、線性式的認定與理所當然嗎? 所以重點是為何佛洛伊德會有這般自信認為這種“殺摩西”造成的歷史創傷,就是導致“殺基督”這種“回饋行為”的原因? 回到佛洛伊德寫就《摩西與一神論》的時空,他是精神科醫生,他的立論在治療上的意義遠大過於找出事件真正原因的意義。它否定類似一神論的極權帝國主義的用意,遠大過於否定類似極權帝國的父權式一神論的用意。他的自信在於他是一位有見地的精神科醫生,他習慣於且必須建立病患對他的信任感。事實証明,它療癒與釋放二十世紀猶太民族在面對屠殺者時並未反抗甚至是自殘情結的用心,遠大過於解釋原罪說是如何產生對殺基督與殺摩西事件的療癒意義。事實也証明,它提醒世人以公義對待猶太人是平等世界公民的意義,遠大過於憐憫背負原罪沉疴的猶太人的意義。只不過,這書在1939年出版之時,學術界、輿論甚至是猶太人自己都反對《摩西與一神論》論調的同時,其實他們忘了他們所面對的敵人應該是“極權式帝國主義的不公義”,而非佛洛伊德。
思惟方法中的縯繹法,已經因為線性式因果關係的狹隘,而遭揚棄,因為它經不起各種可逆性的考驗。佛洛伊德則是直接訴諸逆向的推論,認為殺基督就是全民一起對於長久歷史之前的殺摩西事件的“壓抑事物的回饋”。殺基督的原因與意義,其實應該是有多元面相的。因此佛洛伊德的立論,是過於一廂情願、線性的認定。但是回到1930年代,佛洛伊德提出一神論觀點的時空環境來說,包含帝國主義式的侵略、演化論的線性發展,不也同樣是過於一廂情願、線性式的認定與理所當然嗎? 所以重點是為何佛洛伊德會有這般自信認為這種“殺摩西”造成的歷史創傷,就是導致“殺基督”這種“回饋行為”的原因? 回到佛洛伊德寫就《摩西與一神論》的時空,他是精神科醫生,他的立論在治療上的意義遠大過於找出事件真正原因的意義。它否定類似一神論的極權帝國主義的用意,遠大過於否定類似極權帝國的父權式一神論的用意。他的自信在於他是一位有見地的精神科醫生,他習慣於且必須建立病患對他的信任感。事實証明,它療癒與釋放二十世紀猶太民族在面對屠殺者時並未反抗甚至是自殘情結的用心,遠大過於解釋原罪說是如何產生對殺基督與殺摩西事件的療癒意義。事實也証明,它提醒世人以公義對待猶太人是平等世界公民的意義,遠大過於憐憫背負原罪沉疴的猶太人的意義。只不過,這書在1939年出版之時,學術界、輿論甚至是猶太人自己都反對《摩西與一神論》論調的同時,其實他們忘了他們所面對的敵人應該是“極權式帝國主義的不公義”,而非佛洛伊德。